网上有关“蔡畅的轶事典故”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蔡畅的轶事典故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蔡畅从小向往进学堂读书。蔡母葛健豪慈祥刚毅、豁达明礼、好学上进。1913年底,倡导女子教育的革命思潮席卷湖南,湘乡县第一女校开始招生的消息传到永丰镇。蔡母便和子女们一起到湘乡第一女子学校读了一学期,由于筹措的学费用得差不多了,又没有其它的生活来源,全家人只好回到永丰镇。蔡母想到家乡的女子上学是多么困难、多么不易,又不可能都跑到县城里去受教育,于是就召集子女在一起谈了想在永丰镇办一所女子学校的想法。蔡母的话得到孩子们的赞同。不久,永丰镇上就挂出了“湘乡县立第二女校”的牌子。
蔡畅在创办的这所女子学校里,扮演了双重身份,她平时是学校里的学生,跟随同学们一起学语文、数学等,到上音乐、体育课时,她又以学校的“老师”身份去教大家。由于蔡畅天资聪颖,师生反映都挺好。
学校的教室是由尼姑庵改的,十分简陋。上音乐课时,由于13岁的蔡畅个子矮小,站在黑板前面看不到后面的同学,而后排的学生也望不到她们的小老师。蔡畅为了能让女孩子们集中精力,又能使自己指挥全局,就搬来一条板凳,站到凳子上教学生们唱歌。蔡畅讲课的时候,态度十分认真,也很有耐心。这位小老师和学生们的年龄相仿,很能掌握女孩子们的心思,虽然她的授课经验不多,但她肯下苦功夫钻研,学生们听她的课非常轻松愉快。大家都喜欢她们的这位小老师。新型女子学校遭到当时封建势力的反对,开办不到三个学期,就被封闭了。蔡畅又陷于失学的痛苦之中。 第二女校停办以后,蔡畅一边随母亲从事家务,一边自学文化。生活使她开始感到做人不容易,做一个女人更不容易。她思索着,如何能像她的哥哥蔡和森一样,走自己想走的路。就在她找不到出路,被无穷的苦恼困扰的时候,一个新的难题又摆在她的面前。蔡畅的父亲蔡蓉峰因为坐吃山空,经济窘迫,便想在女儿身上打主意。他看到蔡畅已出落得端庄文雅,品貌双全,便准备以五百银元聘金,将蔡畅许给一个地主家去当小媳妇。
蔡父借着醉意和蔡畅的母亲商量的这桩婚事。母亲听后,当即表示坚决反对这门亲事,俩人为此争吵起来。蔡父大发雷霆地吼叫起来:“这全是你这死老太婆惯的,今天上学、明天办学,还要上天了,全不把老子放在眼里!……”蔡父越说越火,竟然跳进厨房抄起一把菜刀,叫喊着要杀掉蔡畅的母亲。蔡畅陷入了极度忧伤和迷惘的情绪之中,她仿佛觉得多少年给予她温暖和力量的家庭,对于她已经丝毫没有安全感了。她寻思着以后的出路,蔡畅给在长沙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的哥哥写信,叙述了家里发生情况,并提出她想到长沙去躲避的意见。不久,哥哥回信支持妹妹出走的举动。1915年初,蔡畅在母亲的帮助下,瞒着蔡父离开了永丰镇。从此,她再也没有回过那片令她伤心的土地。 尽管党和农民(落后农民)在妇女的身体(去留)之上和颜悦色地争夺,而妇女到底是在利用这一空隙开始狡黠的报复了。她们通过党的《婚姻法》(1950年的习惯称呼是“毛主席的婚姻法”)来报复丈夫翁姑的压迫, 同时通过报复丈夫来破坏他与党的结盟,从而报复党对其身体的利用和分配。这一狡黠的报复,带来了两个后果:1.党像发现落后的“农民意识”一样,发现了落后的“妇女意识”,从而展开了“新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讲习班,和教育农民一样开始教育妇女。以至于后来发展到在浦安修总结中的,利用妇女的善感和自私来做妇女工作和完成政治任务。2.党开始收紧对妇女离婚解放的纵容,试图重新与农民(仍然有很多落后农民)结成可靠联盟,包括在妇女离婚上的联盟,以巩固革命胜利时对妇女身体的重新分配。
这时党的婚姻立法开始普遍修改,先是从“离婚的绝对自由”退回到“离婚自由”。即在“婚姻法”中的离婚自由原则下,列举了离婚条件,实际上就是项英反复批判的“正当理由”。由此可见***在策略上对农民的让步。如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婚姻法》规定了11条离婚条件,如“(1 )夫妇间有一方患残废、癫狂或暗疾,经调查实在的;(2 )妇女如有受翁姑丈夫压迫情形,经乡苏维埃证实的……”1940年《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规定了9 条离婚条件,同时规定了夫妻感情恶劣至不能同居者,任何一方均可诉诸离婚。至于“朝秦暮楚”现象,(被项英贬斥为国民党训政的观点),后来也证明不是空穴来风,在根据地时期,牛山县有一个妇女,三年结离了5 次婚,以至浦安修号召妇女工作干部,“要教育妇女和农民,勿拿婚姻当儿戏”。鄂豫皖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婚姻问题决议案》规定,“男女主谋提出离婚不得过三次……”有的地方还规定:“离婚后经两个月始可再次登记结婚”。在上文提到的《关于婚姻问题决议案》中,苏区中央批评了“朝三暮四”、“一杯水恋爱”现象。还有向荣提出的离婚后男子对妇女的抚养义务显然过苛的问题,苏区也开始纠正,在湘赣省《婚姻条例》中规定:“……(工)中农及中农以下的老婆,实行离婚之后,在未结婚之前,其间的生活,男子概不负责,离婚时只能带本人的土地及衣物。”
显然,***最终放弃了与妇女的结盟,而恢复了与贫农的共同针对“狡黠的媳妇”的联盟,可能是当时苏区或解放区军事危机趋重的缘故,贫农的参军是党的政权得以生存的有效保证,而限制革命初期的大规模妇女离婚便是迫不得已的了,尽管这将会影响基层妇女干部工作魄力的展现。但***并没有放弃妇女解放的工作任务,而是终于在蔡畅、浦安修等一批坚定而又智慧的女干部的出色努力下,实现了“温柔”的转变。
法律转型的同时,作为重要舆论力量的宣传口号也开始转变。著名美国记者斯特朗曾记述道:“妇女运动的领袖蔡畅对我说,‘我们在农村地区的口号不再是婚姻自由和妇女平等,而是拯救婴儿和家庭和睦了。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把女权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结果引起了农民的反感。男女之间的矛盾削弱了反对日寇和地主的共同斗争’”。
1940年至1942年左右,许多文件、资料和法令中都开始大量地谈论爱情和幸福的“慎重”。同一时期,蔡畅、浦安修等妇女干部,也以“家庭和睦”口号换掉了“婚姻自由”。
这个记述是如实的。浦安修在《总结》中也着力分析了这一点。(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蔡畅和浦安修的思想是较为接近的)。浦安修非常聪明地分析了农民和妇女的关系,认为“妇女运动的口号须依靠农民的觉悟程度来提出。” 这也表明当时的***的策略转换上,农民的利益终于高出了妇女的利益。这人们不应以女权主义的立场来判决浦安修和蔡畅的“变节”,在当时的中国农村,这种提法反是务实的,真正关心妇女的。因为这个口号“正可以解放妇女不少的痛苦,并易获得各种人士的同情,尤可得到老年妇女的同情……”。
但是在客观上,“家庭和睦”的口号使得革命对当时的婚姻家庭,尤其是贫农的婚姻家庭的策略成为一种看守和维系。不是通过打破而是通过营造,来求得妇女的安全、少痛苦,来求得家庭,以至整个解放区的安全、少痛苦。
1959年,一次特别的会议上,沸反盈天。
“未经请示,擅自调动上百个团的兵力,发动百团大战,战后遭受日军报复,使华北根据地和我军的发展遭受了严重挫折,不是明摆着帮了蒋介石的忙吗?”
第一个混不讲理的,开始了。
紧接着,脏水如暴雨倾盆般地不断袭来。
“皖南事变新四军被歼,毛岸英的牺牲,……,你要负全部责任!”
其实,人言之所以可畏,怕的就是白成了黑,再或者是“莫须有”,它像一把把剔骨刀,精、准、狠地剜进了人的心里。
而老帅,还是那个脾气,眼里揉不得沙子,直来直去,拳头重重地落在了桌子上,用一声怒吼进行了最后的反击。
"我的罪在消灭了几万日本侵略者!"
然而,他还是失败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正确。
谁也想不到,这个曾经敢横刀立马,让老对手冈村宁次和麦克阿瑟都闻之色变,煞费苦心想要除掉的悍将,就那么稀里糊涂地倒在了自己人的手里。
迫害和毒打,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从未停止过。从四川返回北京后,仅仅4年的时间里,老帅就遭受了250多次的批斗,肋骨被打折了,肺也被踢破了。
人民站了起来,而他却瘫痪在床了。老帅的经历有多凄惨,恐怕将汉语词库的形容词全部用上,也未必能完全表达出来。
1973年春天,八年的铁窗生活和无情折磨,使老帅患了直肠癌。癌症产生的疼痛,非常人能忍受,尽管老帅咬牙硬挺,用嘴撕烂了被单,仍然无济于事,却不得不哀求看押士兵: "给我一枪吧!"
……
1974年11月29日14时52分,老帅眼角挂着两行泪水,在一声长叹中,于北京301医院14号病室的5号病床上将星陨落,时年76岁。
四年之后,
1978年12月22日,成都的双流机场内,愁云惨淡 。在一片哭泣声中,一个贴有“王川”姓名的骨灰盒,由工作人员双手抱着,缓缓地登上了飞机,送往北京。
12月24日,一场隆重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前来参会的人员,除了党和国家的***以外,还包括2000多名首都的群众代表。
那么,骨灰盒上的王川是怎么回事,为何会引起如此大的轰动?
1974年11月29日14点25分,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彭德怀带着最后的执拗和尊严,在没有任何亲人和朋友的陪伴下,悄然而逝。
第二天,老总的侄女彭梅魁前往与遗体作了最后的告别,接到的消息却是,不能发出哭声。
匆匆地告别后,彭德怀的遗体就被悄悄运往了一个秘密的地方进行了火化,以至于,彭梅魁都不知道大伯骨灰的去向。
老总的骨灰究竟去了哪里?
原来,这一切,离不开一个人的用心良苦。
前文所说,长期的无情折磨,使得彭德怀身患癌症,而许多医院得知他的身份后,果断选择了拒诊。周总理听到这一消息后,不顾自身的处境险恶,将彭老总安排到了解放军301医院医治。
当然,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彭老总也只有周总理,这么一位可靠的战友了。
在周总理的关照下,彭老总很快得到了医治,但一听说,要给自己动手术时,彭老总坚决不同意。老总认为医生们为他冒那么大的风险,完全没有必要,如果治不好,可能还要受处分。
最终,在医院副院长苦口婆心的劝说下,彭老总这才勉强接受手术治疗,但前提是要同意他的三个条件:
看看吧,这就是彭德怀元帅,到这种时候,都不忘守土卫国,反观当年那些对他拳打脚踢的年轻人,他们干了些什么?
前两个条件,显然不能实现了,彭老总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再大书特书了,而周总理除了夙兴夜寐,身体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值得庆幸的是,彭老总在和侄女彭梅魁长谈过后,决定进行手术治疗。
晚了,真的太晚了。癌细胞早已扩散到彭老总的肩部、肺部和脑部,手术治疗不过是,让昙花一现。
彭老总最终还是走了,他的脚上没有穿袜子,脚趾从鞋前的破洞里露出,而身上所穿的,仅有一件黑色的破旧单薄棉衣。
面对战友的离去,周总理摧心剖肝,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彭老总的骨灰,周总理安排好一切后,当即决定将化名为“王川”,实为彭老总的骨灰,运往四川成都,与普通群众的骨灰盒,存放在一起。
就这样,两名身着军装的办事人员,抱着彭老总的骨灰,带着周总理的十六字批示,乘坐飞机,秘密向成都飞去。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四川成都,而不是其他地方呢?其实,从这里也不难看出,周总理为了保护战友的骨灰,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
1965年9月,彭德怀与妻子浦安修告别,踏上了前往四川的列车,出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
在那里,彭德怀依旧顾全大局,兢兢业业,直到被闪电般地带回了北京。
而任何人都会退出 历史 的舞台,周总理自然不能例外,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希望假以时日,后来的人们能够通过这个线索,进而找到彭老总的骨灰。
“精心保管,时常检查,不准换盒,不可转移。”
正是因为周总理这份短短的批示,很多事情才得以顺利地进行。
1974年12月下旬的一天,负责运送彭德怀骨灰的办事人员,径直来到了四川省政府的大门口后,对着门口的警卫指名道姓,要见时任四川省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省委书记、省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大章,省委书记段君毅。
门口的警卫,一看这架势,哪敢慢待,立即选择了上报,而刘兴元、李大章和段君毅三位省领导在接获消息后,心领意会,意识到一定是有大事发生了,赶紧出门相迎。
果不其然,双方坐下后,其中的一位办事人员开口了: “按中央领导的指示,我们送来了这个骨灰盒,内装彭德怀的骨灰,经组织决定,更名王川,送到成都存放。骨灰盒不要特殊对待,放在一般群众存放骨灰盒的地方……这些情况,你们三位知道就行了,不准向任何人透露,要绝对保密。”
临行之际,两个办事人员,再三强调了周总理的十六字批示过后,才放心地离开了,前往锦江饭店的38号房间下榻。
刘兴元、李大章、段君毅听闻噩耗后,都犹如被人打了一闷棍,眼前一片漆黑。好长时间,三个人都默不作声。尤其是李大章,彭老总在四川工作期间,还就三线建设的一些事情,多次与他交流过。一阵莫名的痛,淤积在李大章的胸口,久久难以消去。
既然彭老总“来了”,抛开上面的指示不说,也该尽心尽力,将他的骨灰安置好。
随后,三人收起悲痛,经过一番商议,决定将彭德怀的骨灰安全转移到成都东郊火葬场,具体工作由段君毅负责。
然而,段君毅身患美尼尔氏病,旧病复发,卧床不起,所以,他只能将这个重大任务,交给省委办事组组长杜心源。
段君毅语重心长地对杜心源说:“你要尽快安全地把这个骨灰盒转移到成都东郊那个火葬场去存放。要向火葬场的同志讲清楚,要绝对保证骨灰盒的安全。骨灰盒存放好后,没有省委的批准,任何人不准移动,不准更换盒子;你还要经常去检查它的安全……周总理是有指示的,千万出不得差错。你们必须保证:一是绝对安全,二是绝对保密。”
说罢,段君毅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悲伤,眼角盈满了泪水。
杜心源不敢松懈,当下找来了办事处的副组长张振亚,将具体事宜吩咐了下去。
而后,张振亚与革委办事组行政处的副处长杜信取得联系,让他驱车前往锦江饭店,同北京来的两个办事人员,办理骨灰的具体交接。
在锦江饭店的38号房间里,杜信接过了那个神秘的,由粗木板打造、平平无奇的骨灰盒,只见上面贴有一个小纸条,清晰地写着:王川,男。
为了保密起见,杜信将骨灰盒装入黑色的手提包后,马不停蹄地来到了成都东郊的火葬场,找到了负责人辛自权,两人进行了一番秘密交谈。
辛自权是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在火葬场干了大半辈子,从杜信的话语中,他不难听出,骨灰盒里面装着的,一定不是普通人,再加上省委如此重视。辛自权顿时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
因此,辛自权认真地写下了一张骨灰寄存单: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后来,辛自权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却仍然坚持,每周骑自行车查看一次“王川”骨灰盒的存放情况。
杜信将骨灰存放以后,立即找到了杜心源,并向他汇报了骨灰盒的存放情况。
事实也证明了,张振亚用人得当。
杜信办事干练,极具远见性,因此,张振亚才将骨灰安置一事,交由他办理,这也为日后找到彭德怀的骨灰,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杜信在与杜心源汇报工作时指出:“心源同志,一切都办好了,骨灰盒的存放编号是237号。但是,万一骨灰要取,要凭卡才能取得出来。现在骨灰盒寄存卡怎么保存好?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保险?”
是啊,放在谁的手里,都不合适,时间久了,谁能保证不丢了呢?
大家越想越急,直到有人提出,为什么不存放在省革委会办事组档案室,登记入册,作为重要档案保存呢?
杜心源觉得可行,随即找来了负责档案的何淑谦,将骨灰盒寄存卡列为机密,封存入档。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陈云的提议下,中央重新审查了彭德怀的旧案,并纠正了对彭德怀的错误结论,作为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建树的伟大功勋者,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为彭德怀举行隆重的追悼会。
可问题来了,彭老总的骨灰在哪里?没有骨灰还怎么开追悼会?又如何向世人交代?众人再次陷入了无尽的悲痛当中。
然而,就在工作人员苦苦寻求彭老总骨灰未果的时候,彭老总的妻子浦安修,找到了陈云,道出了一个惊天秘密。
彭老总的骨灰在成都!
那么,浦安修又是从哪里得知,丈夫骨灰的下落的呢?
1975年,原四川省委书记李大章,被调往北京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令人意外的是,李大章的妻子孔明和浦安修关系却非同一般,早在太行山西北局妇女委员会时,二人就是无话不谈的闺蜜。
来到北京后,孔明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望了浦安修。面对强大的压力,浦安修早已褪尽风华,孔明实在不忍心看着老战友悲伤难过,道出了一些关于彭老总骨灰的实情。
事后,李大章得知妻子同浦安修提及了此事,便不再隐瞒,干脆一五一十的全部告诉了浦安修。
有下落了,总算是有下落了。专案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火速赶往了成都。
负责接待工作的是张振亚,当他接过介绍信后,先是愣了半天,而后才有气无力地说:“彭德怀来四川工作,我是清楚的,但从没有听说过他的骨灰盒存放在四川呀!你们是不是弄错了?”
专案组的工作人员,既失望,又着急,但还是决定再试一试。
“1974年冬天,有没有两个解放军,从北京送了一个骨灰盒来成都存放?”
“有!当时的省委常务书记段君毅同志和杜心源书记,亲自交我们几个人办的,但是,那却不是彭德怀同志的骨灰盒,而是一个叫‘王川’的骨灰盒!”
“对!‘王川’的骨灰盒,就是彭德怀的骨灰盒!”专案组工作人员,一语打破谜题。
随后,专案组的工作人员,也顾不得核实了,立即动身,回北京复命。
专案组的工作人员走后,张振亚赶忙找了杜心源,并告知了实情。
杜心源的内心崩塌了,他伏在办公桌上抱头一顿痛哭。过了好久,他才停了下来,红肿着眼对张振亚说:“段君毅同志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保护彭德怀同志的骨灰盒,他想得细,考虑得周到,组织安排得当,指挥若定,是立了大功的呀!
一定要妥善保护好彭德怀同志的骨灰盒,同时还要继续保密,听候中央安排。”
12月22日,在成都东郊的火葬场里,静静躺了整整四年的彭老总,终于迎来了沉冤得雪的日子。
在成都的双流机场里,前来接彭老总骨灰的飞机,早已停放好了,四川省省委、军区的领导无一不落,纷纷赶来,同彭老总的骨灰,作了最后的告别。
杜心源在他人的搀扶下,哭嚎不止,用颤抖的双手捧过彭德怀的骨灰盒说:“彭老总,您一路走好啊!”
而后,在全体人员的三鞠躬中,载着彭老总骨灰的飞机,离开了成都。
飞机来到北京后,飞行员还特意在上空绕了一周,最后在西苑机场降落。
前来迎接彭老总的亲属、旧部和军委首长,在舱门打开的那一瞬间,早已哭成了一片。
12月24日,彭德怀的骨灰盒在成都隐姓埋名整整四年后,终于盖上鲜红的党旗,堂堂正正地摆放在了主席台的正中央。
“ 历史 是最无情的。 历史 会审判他们,也会对我做出公正的评价。” 这是彭老总生前最后的呼声和愿望。
是的,彭老总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可惜的是,他却没能等到这一天。
纵观彭老总的一生,他从不计较个人恩仇,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对革命工作勤勤恳恳,极端负责。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彭老总仍不忘洗刷完自己的冤屈,再以清白之身,出来为人民工作。
彭德怀元帅,永垂不朽!
关于“蔡畅的轶事典故”这个话题的介绍,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完了,如果对你有所帮助请保持对本站的关注!
本文来自作者[语凝]投稿,不代表博羽号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sz-boyu.cn/sz/2190.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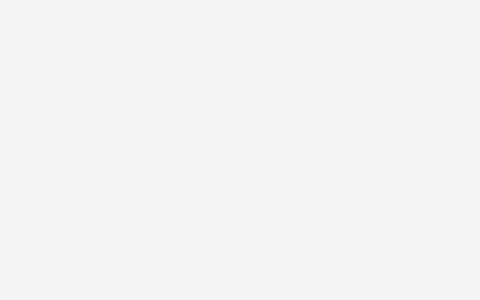
评论列表(4条)
我是博羽号的签约作者“语凝”!
希望本篇文章《蔡畅的轶事典故》能对你有所帮助!
本站[博羽号]内容主要涵盖:生活百科,小常识,生活小窍门,知识分享
本文概览:网上有关“蔡畅的轶事典故”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蔡畅的轶事典故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蔡畅从小向往进学堂读...